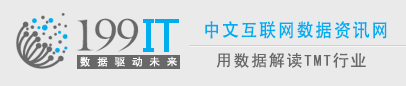我在八月切断了与Facebook、Twitter、Instagram、商务社交网站LinkedIn、Pinterest和MessageMe的联系。如果你想在九月前联系我,请往我的《财富》邮箱发邮件,或者最好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比以前更多的时间来给你回电话。
简单地说,我想知道自从2003年首次登录Friendster以来,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在我拥有头像照片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自从2005年在《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上发表第一篇关于社交网络的封面文章以来,我一直在撰写关于社交网络工具的文章——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工具。通过离开这一个月,我希望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技术,同时撰写一批有意思的文章,谈谈它们如何塑造人类的未来。
大家或许没有注意到,逃离网络在今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今年五月,保罗•米勒供稿The Verge网站,分享了远离网络一年期间的生活经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文介绍了戒除数码瘾的训练营,而《快公司》(Fast Company)的封面故事也是关于一个离开网络25天的男人。说真的,这个故事还挺吸引人。
我相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是因为美国的网络用户已经达到了最大量的社会过载。我把它归功于一系列完美的新型工具——智能手机、平板电脑、Up bands、Fitbits,噢——甚至是谷歌眼镜(Google Glass),以及一系列人们认为不可或缺的新型服务,即使Facebook这样的老式服务依然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按照以下顺序逐一翻看:短信、工作邮箱、Gmail、雅虎、Instagram、Facebook、Twitter,之后是我iPhone通知面板上的其他信息。
就像对待其他技术一样,我们需要搞清如何让社交服务融入我们的生活(我广义地将包括电子邮件和短信在内的、所有核心内容依附于社交网络的服务定义为社交服务)。还记得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手机的时候吗?几年间,我们就让它们在餐馆和电影院中响起,还因为接电话而中断了彼此的交谈,直到后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文化准则,规范了如何使用它们。而由于这些社交服务本身进化得如此迅速,这一系列文化准则也更难约束它们。
这几年来,每年春天,我都在寻求逃离网络的一次国际度假,从而让自己摆脱每次感到震动都会把手伸进口袋的条件反射。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躲在小窗后的孤独生活让我觉得颇有滋味,不过即便是这些遥远的地区也与网络联系紧密。(几年前,我关掉手机,挎起背包,徒步去往土耳其南部海岸一家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馆,不料却在那里碰上婚宴。人们正随着这样一首流行的土耳其歌曲热烈地舞蹈:“Facebook!Facebook!我在Facebook上遇到了一个女孩!”)
同样,“度假”这个词的定义是离开常规的日常生活。
因此,今年夏天,我决定探寻这项技术对我日常生活的影响。为了减少获取社交信息,我为自己制定了如下规定:
— 常规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半之间查收工作邮件和私人邮件。
— 还可以通过工作电话和手机联系到我。在家里,我准备把电话安在厨房里,那里预留了一个放座机的地方。(2003年6月我扔掉了电话。)
— 任何时候都不登陆社交服务。
— 任何时候都不使用即时通信服务。
— 不发短信。
逃离社交媒体的过程比我预想的要困难。比如说,社交服务不会像我的电子邮件那样提供假期自动回复;毕竟我们一旦有段时间不用它,就可能将它弃之不用。同样,我的社交信息订阅支持着我在网上的许多活动——从在网飞(Netflix)上看电影到使用Seamless订餐。试着把这些事情与网络分离是件可怕的事情。此外,社交不仅是社交,它对我的工作也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在本月重要的商业会议之前,我会渴望使用LinkedIn,就像我去年夏天尝试在晨间咖啡时间里戒掉对咖啡因的渴望一样。那种感觉不会好受的。
但我计划在这一过程中做下记录,借此更加了解自己——同样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我使用的社交技术。我将在本月底分享这些想法。我也期待听到你们对于类似体验的想法。如果对此事还有其他关注,可以通过“蜗牛”邮件寄给我……
更多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