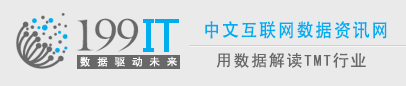文/摘编自《逃离不平等》 作者 安格斯-迪顿(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者 崔传刚
贫穷国家的工资水平当然较低,这正是穷国的一个特质,但是过分夸大它们相对于富裕国家的贫困水平却没有任何益处。
要对物质生活水平进行评估并非易事,即使“收入”这个日常用词其实也非常难以确切定义。除此之外,贫困、不平等这些方面的评估标准,也未必比收入的评估标准更清楚;在进行跨国比较时这种困难会更为显著。怎样的收入水平就可以免于贫困?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居住的人对这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即使是国家贫困线也无法确切反映在某个具体社会生活的基本成本,况且,不同的群体对于需求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多数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将贫困线视为一个判断能否生存下去的合理数字。
但如果我们要对全世界范围的贫困进行评估,就需要确立一条在全世界范围都合理的贫困线——既适合肯尼亚的内罗毕和厄瓜多尔的基多,也适合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马里的廷巴克图。
当然,它也需要适合发达国家的城市,譬如英国的伦敦和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要做到这一点,以便对全世界的收入状况进行对比,就需要能够对不同的货币价值进行等价换算。也许我们会将等价换算的实现寄托于汇率,不过,汇率本身对此无能为力。
一种货币如何才能等价转换为另外一种,比如美元如何才能变成印度卢比?这里存在一种每天都会变化的叫作汇率的东西,它表示在市场上1 美元能够兑换到的卢比。比如在2013 年4 月,美元兑卢比的汇率是1∶54.33 。
这意味着,如果我从纽约飞到德里然后在银行柜台前进行兑换,将可以用1 美元换得大概50 卢比。当然,因为银行需要从中赢利,所以我换得的卢比可能比这个数字少。
但是,当离开机场进入城区,我发现,即使是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我用50卢比能买到的东西也比在纽约用1 美元所能买到的多得多;而如果是在德里经济学院的食堂,或者是在当地街头,50 卢比能买到的食物和1 美元能在纽约买到的食物相比简直是丰盛到叫人无法相信。
简单地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印度的物价水平要比纽约的低很多,如果将货币按照市场汇率进行换算,那么同美国相比,印度的大多数东西都会很便宜。
事实上,根据最新的估算,印度的物价水平大概只有美国的40% 。换句话说,如果美元兑卢比的汇率为1∶20 ,而不是现在的1∶50 ,印度和美国的物价水平才是相当的。这种让1 美元在两地价值相当的“正确”的汇率,被恰如其分地称作购买力平价汇率(PPP 汇率)。
购买力平价汇率是以两地的相同购买力为基础换算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如果印度德里的价格水平比美国纽约的低,则购买力平价汇率会比外汇市场汇率低。多数贫穷国家的物价水平都比美国的低,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平价汇率都具有这种特征。
购买力平价汇率是怎么算出来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基准的市场,所以,计算这样的汇率只能靠统计与发掘。相关研究和统计人员从全球各地收集到数以百万计的物品价格,然后计算出每个国家的平均物价水平。最早进行此类统计的机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20 世纪70 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欧文-克拉维斯、罗伯特-萨默斯和艾伦-赫斯顿首先对6 个国家的平均物价水平进行了计算。多年来,艾伦-赫斯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本书中的很多数据都来自他那里。这些创新者改变了经济学家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如何对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行跨国对比。
在这种跨国研究对比中,我们首先会发现,印度这样的情况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普遍存在;相对贫穷的国家,物价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国家越贫穷,物价水平也相应越低。
很多人认为这个结论不可思议:一个地方的物价水平会比其他地方的低,这怎么可能?如果德里的钢铁或者汽油价格都比纽约的低,那为什么贸易商不去德里买进这些东西然后运到纽约出售?
实际情况是,如果将运输成本、税费和补贴考虑进去,钢铁和汽油等物品在纽约和德里的价格差距其实并不太大;但并非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如此。
比如,德里的理发价格、曼谷的食物价格,放在纽约看绝对非常便宜,但是贸易商对这样的商品或服务却毫无兴趣,这其中是何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服务只在德里或者曼谷提供而不能搬到纽约去。贫穷国家的人民相对穷困,所以这些国家的服务价格也相对便宜,但是,多数价格低廉的服务是无法转移的。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那么富裕国家的工资水平将会下降,穷国的工资水平则会上升,如此一来,整个世界也会变得更为平等。
不过,富裕国家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工资水平下降,因此他们反对人口的自由迁徙;而没有自由迁徙,上述结果就不会出现,穷国的工资水平就会继续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于是那里的服务,比如理发和饮食的价格也就持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也同样无法在穷国和富国之间进行对比。印度或者非洲的住房价格便宜,可是那里的土地不可能搬到美国按照美国的价格进行销售。廉价土地与劳动力的存在,是穷国物价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市场运用汇率手段使得钢铁、汽油、汽车与电脑的价格在各国基本一致,因为这些产品都能够成为且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但是,一般而言,决定平均价格水平的是那些无法交易的物品和服务,而这类物品和服务往往在穷国相对便宜,所以,国家越穷,其平均物价水平越低。
正因为穷国的物价水平更低,如果我们使用市场汇率来比较各国的生活成本,就会导致结果的谬误。新闻报道经常犯这种错误,而经济学家也时常会落入汇率的陷阱。
2011 年春,印度政府在印度最高法院(既不明智又显悭吝地)宣称,印度人,至少是印度的非城市人口,每天只需要26 个卢比就能够摆脱贫困。这一说法随即被媒体大肆炒作,印度以及国际媒体都报道称,世界银行[微博]的贫困线标准是每天1.25 美元,按照美元兑卢比1∶53 的汇率,世行这个标准比政府所定的标准要高出两倍还多!不过,要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1 美元约合20 印度卢比,那么世界银行的1.25 美元贫困线标准—也就是大概25 卢比—就和政府所建议的差不多。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金融时报》,也使用了市场汇率来计算美元与卢比比值,声称印度政府所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实际上只有0.52 美元一天,大大低于世行所制定的标准。
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印度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更为真实的数值其实是1.3 美元,这虽然依然很低,但比起0.52 美元这样的错误说法,这个数字已经翻了接近3 倍。
联合国[微博]开发计划署多年来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一直备受人为夸大贫穷国家人口贫困状况的指摘。当我们谈及贫穷国家人口的生活水平时,只要使用市场汇率,则不论是工资水平、看病费用抑或是交通与食物支出,都会被低估1/3~1/2 。贫穷国家的工资水平当然较低,这正是穷国的一个特质,但是过分夸大它们相对于富裕国家的贫困水平却没有任何益处。
当我们对生活水平进行跨国对比,或者是统计全球的贫困状况与不平等状况时,购买力平价汇率永远是正确的选择。在这里,“跨国”这个词意义重大。当我们计算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时,会认为不调整地区之间的差异是正确的选择。
以美国为例,在堪萨斯或者是密西西比生活的成本当然要比在纽约低,但是别忘了纽约的生活成本虽高,同其他地方相比它提供的便利也多。实际上,如果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那么大城市的高物价水平就意味着这里提供了更多物有所值的便利。
正是基于此,我们在对比跨地域的收入差异时就无须做出价格调整;纽约市曼哈顿区的高收入人群绝对比堪萨斯州曼哈顿市的低收入人群生活得更好。但是跨国的对比,比如要比较印度和美国或者法国和塞内加尔,情况就大不相同,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是不能自由流动的。
即便与在印度生活相比,在美国生活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对于这一点我有所怀疑),也不能因此就认为美国和印度的物价差距是生活质量差距的真实反映。所以,当我们对印度和美国的收入进行对比并以此来评估国家间的差距时,就必须引入购买力平价汇率对物价进行调整。
进行跨国对比时,购买力平价汇率要优于市场汇率,但购买力平价汇率也远非完美无缺。对于不同国家的可比较项目,我们可以在各国收集其价格信息,然后进行计算。
比如,我们可以收集计算河内、伦敦或者圣保罗地区1 公斤大米的价格或者理一次头发的价格。但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很容易地进行对比定价。比如,一个贫穷家庭在农村的自建房屋应该定价多少?在城市贫民窟搭建的一顶帐篷又该如何定价?富裕国家存在着多层次的房地产租赁市场,然而在贫穷国家,这样的租赁市场还没有形成,因此定价极为困难。
在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等由政府提供的国民服务都非常难以定价,而要对这样的服务进行跨国对比就更是难上加难。国民消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对于这样的项目我们只能靠估算—这虽然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但是其结果也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回归通常的汇率计算方式,毕竟我们已经知道那种方法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要清楚,虽然购买力平价汇率更为准确,但是它也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存在。
对不同国家可对比项目的价格统计,还有需要进一步反思的地方。以男士衬衫的价格为例,在美国,一个标准的统计项目或许是一个知名厂商生产的衬衫,比如一件布克兄弟(美国经典男装品牌)的牛津棉布衬衣。
拿着这件衬衣与玻利维亚、民主刚果或者菲律宾等国家生产的男士衬衣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自己最终将陷入两种都无法令人满意的选择。在这些国家,一件标准衬衣的价格一般都会很便宜,但是质量也要比布克兄弟的差不少。
因此,如果将两者进行对比,实际上并不是在对比两种同样的东西,如此一来,我们就会低估穷国的物品相对于富国的价格。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在这些国家费尽全力找出和布克兄弟类似质量的衬衣再进行价格对比。这样的衬衣,或许只在这些国家首都最好的商场里有售。
但是这样的对比又会有相反方向的风险:我们能够在这些国家找到这样的衬衣,然而,这样的衬衣只在这些国家最贵最高档的商店中出售,且只有为数不多的权势人口才穿。这样,至少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高估了这些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此,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开始进行拔河比赛:是只统计国与国之间可对比项目的价格呢,还是只统计人们购买的有代表性的商品价格?极端情况下,如果在一个国家意义重大且使用广泛的商品,在另外一国全然不存在,那么这种对比就会失效。
比如,画眉草是埃塞俄比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作物非常鲜见;豆腐是印尼人的日常食品,但印度人就很少吃;因为宗教因素,很多伊斯兰国家都没有酒类产品出售。
即便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可获得,不同国家的人对不同的商品也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也不尽相同。我在英国长大,如今却住在英国之外。这里就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在英国,有一种几乎可以归为生活必需品的食物叫作马麦酱。
这是一种非常咸的酵母萃取物,是酿酒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最早由路易斯•巴斯德发现,随后被授权给一家英国的啤酒生产商生产。在英国,马麦酱价格便宜且消费量很大,卖的时候都装在大黑罐里;但是在美国,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虽然马麦酱也能买到,但价格变得很昂贵,而且包装也换成了小的。
马麦酱是一种定义明确并且可以进行精确对比的商品,在英美两国,它的价格也很容易统计,但是,英国人对马麦酱的消费量要比美国人多很多。
所以,若是以英国人的商品消费习惯来计算对比英美两国的物价水平,就会发现美国的价格水平要比英国的高;反过来,美国人热衷的全麦饼干和波本威士忌在英国没什么销量,价格也相对要高,若是以美国人的商品消费习惯来对比两国物价,那就会得出英国物价水平高于美国的结论。
英美这类富裕国家之间差距较小,所以无论是使用美国的商品进行比较,还是使用英国的商品做比较,其结果都不会有太大差异。但是,马麦酱这个例子说明了进行跨国物价比较的一个基本问题:每个国家都会消费更多在其国内相对便宜的商品,而对那些相对昂贵的商品消费较少。
因此,如果用国内“一篮子”商品的价格为基准来评价国外的消费水平,就难免有高估国外生活成本的风险。如果我们以国外的“一篮子”商品价格为基准,则又可能低估了国内的相对成本。在实践中,统计人员往往折中,以求出一个平均值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折中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当我们将英国的物价水平同西非国家喀麦隆的进行对比时,这一点就清晰可见。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在喀麦隆乘飞机旅行非常昂贵,因此使用航空旅行服务的人很少。
但在英国坐飞机就很便宜,即便是相对不怎么富裕的人也可以乘飞机到国外度假。以喀麦隆的航空价格来衡量英国的价格水平,就会显得喀麦隆的物价极高。
折中一下将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无论如何,航空价格水平还是对喀麦隆的购买力平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喀麦隆的航空服务近乎为零,但如果将航空价格考虑在内,则喀麦隆的物价水平还是会高出2%~3% 。
在包括贫困评估等在内的一系列情境中,跨国物价的对比常常要依赖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这真是极为荒谬的。在这里,英国和喀麦隆的问题就在于两个国家的差别太大了,而英国和美国之间就没有这么大的差距。
不过,与中美之间的物价水平差距相比,英国和喀麦隆之间的差别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依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测算,2011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 455 美元,美国的则是48 112 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中国的9 倍。
但是,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以市场汇率计算的,没有考虑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美国的2/3 这个现实。如果改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个更好的指标,我们将会发现,美国人的收入只有中国人的5.7 倍,而不是8.8 倍。对于军人或外交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更多是依靠其资源总量,因此他们更关心这两个国家的绝对经济总量。
而要计算这一数值,就需要根据中国人口与美国人口的数量比例将中国的数值乘以4.31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总量为美国经济总量的3/4 。
考虑到中国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且会保持这种趋势,可以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能一直保持比美国的高5 个百分点,那么中国超过美国只需要6 年。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对于数据的使用建立在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市场汇率一样可获得的基础上。但是我们知道,马麦酱的问题、喀麦隆的航空旅行问题,以及对典型的可对比项目进行类比时所产生的不确定性,都会影响购买力平价数据,真实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可能会比我们的数据更高或者更低。
在与艾伦-赫斯顿展开合作研究时,我们发现,如果将类似马麦酱的问题考虑在内,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考虑用中国或者美国的“一篮子”商品来对价格数据进行平均,则计算所得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将会有大约25% 的误差。
所以我们只能说,2011 年,按照国际元计算的中国人均收入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3%~22% ,而在总量方面,中国是美国的56%~94% 。当然,这样的数据范围太大,如果做一些折中处理,得到的结果将更便于使用。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折中毕竟是针对那些没有完美解决方式的概念性问题的一种比较武断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这一特殊的例子中,还有其他问题影响着最终结论的准确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那个长期存在并仍未尘埃落定的争论: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其数据是否可信?很多学者都有这样的猜疑。那么,如果数据真有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这样的数据进行调整?
我不想给大家留下一种跨国对比难以展开的印象,也不想让结果总是存在太大的误差。1949 年,我当时的导师——剑桥大学的理查德-斯通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对美国和中国或印度等国家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呢?这里面有何可能的利益关切?谁都知道从经济层面看,一个国家非常富裕另一个国家非常贫穷,但它们之间具体的差距是30 倍40 倍还是其他,这样的事情重要吗?”
时至今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水平已经大大高于1949 年时的情形,不用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就是大众媒体也一直在关注到底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超越了美国。
此外,同我老师的时代相比,如今我们在数据收集以及思考方法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想知道,富国和穷国之间到底差距多大。当然,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当我们将富裕国家和中国、印度或者更为贫穷的非洲国家进行对比时,这一点更为明显。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类似,相互对比时不确定性相对较少,因此下结论时较有把握。
比如对于加拿大、美国或者西欧国家而言,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汇率的差别就比较小,因此在对这些国家进行对比时,我们的立论基础就比较牢固。
(本文作者介绍:由中信出版集团打造的文化服务品牌,我们是新知识的传播平台,新思想的争鸣平台,新文化的建设平台。)
更多阅读: